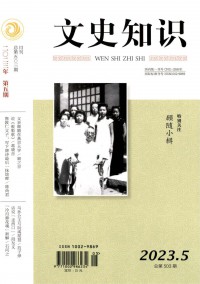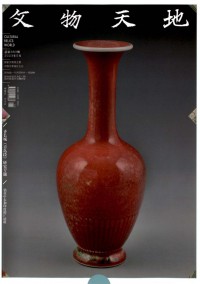考古學的重要性匯總十篇
時間:2023-11-27 10:11:22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考古學的重要性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這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本來是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現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來他引述了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劉先生接下來評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現相聯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回顧近現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篇(2)
1)考古和媒體的合作歷程。
考古和媒體合作的歷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為將考古和媒體聯系到一起的創始人,揭開了考古和媒體的新歷程,并為此做出了卓越貢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秉琦作為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也首次主張應建立考古學的公眾傳媒意識。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家和媒體對考古的關注度日益加深,公眾考古和媒體和合作逐漸鍵入確立階段。
2)公眾考古傳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
在考古傳播中,公眾對考古學科知識的了解日益加深,但與實際的考古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考古學具有嚴謹、理性的學科特點,而傳播學具有感性、通俗的學科特點,兩者存在沖突;‚考古學和媒體界存在不一樣的職業特性,考古學更注重條理、學術,而媒體更注重趣味和時效;‚考古界和媒體界在價值需求方面存在差異,考古界注重對過去的研究,而代表大眾的媒體在考古上的鑄就更強調對知識的了解和對傳統文化的感知。
3)公眾獲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徑。
通過調查研究,目前大眾對于考古知識的了解是比較客觀的,但仍然與考古有一定的距離感。公眾主要通過大眾傳播媒體來獲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學者和傳媒的沖擊下,對遺產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識。因此作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傳播考古學的責任感,并通過與媒體的互動與合作,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滿足公眾需求。
2、考古學大眾傳播的類型
根據不同的傳播介質,將考古學大眾傳播分為四種類型:平面印刷媒體,例如雜志、圖書、報紙等;廣播媒體,例如電臺、電視等;數字媒體,手機、互聯網等;娛樂媒體,包括以上各種以及電子游戲、唱片等。在我國,考古學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等進行傳播,數字媒體和娛樂媒體也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們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剛興起的新媒介,在大眾中有極高的關注度而且傳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兩種傳播方式的基礎上,更加重視后兩種傳播方式。
二、考古學大眾傳播下的媒介倫理
1、考古學的學科特征與職業規范
考古學的學科特征比較復雜,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間的學科,主要是對古代遺物和文化以及人類的生活狀態進行研究。現在隨著考古技術的不斷發展,考古研究也應用了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現在隨著考古技術的不斷發展,考古研究也應用了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考古學帶有自然科學的特征,所以我們在研究公眾考古學傳播目的過程中,應該充分認識考古學的學科特征,然后具體分析傳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眾傳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且出現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眾考古工作的行為,但是我國還沒有專門從事公眾考古傳播研究的人員,所以需要組織和培養一批專職公眾考古人員。為了保障公眾考古從業人員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制定相應的職業規范,比如《文物保護法》、《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等;另外一方面,還需要一些區別于一般性的考古規范,要滿足:第一,專業性,就是要求公眾考古從業者是受到考古文博類專業教育的人員;第二,傳播性,公眾考古人員應該認識到自身工作的大眾傳播性;第三,實踐性,能夠積極實踐多種傳播模式。
2、媒介倫理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分析,媒體工作者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責任,所以需要制定相關法律來約束媒體行為,并從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倫理問題,加強媒體從業人員的責任感。道德是針對個人自主和自愿行為的,也為實踐者提供了道德借鑒,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論依據,作為公眾考古傳播的媒體合作者,更應該強調絕對倫理,采納義務論倫理,在行動中遵循一定規則。媒體應該具備將考古信息提升為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的高度,遵循媒體職業道德,突出媒體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為公眾提供真實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體自身的社會公信力。
3、考古與媒體的信息交流
對于媒體從業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學,本文認為媒體從業者應該首先重視考古學學科的特質,尊重考古學的實證性、考古工作的學術性、漫長性,將自己對考古信息的價值訴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這樣就能夠獲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賴,實現雙方的有效溝通。另外,媒體從業者應該對社會和公眾負責,明確考古信息的客觀價值,并給予真實報道,雖然一些虛假報道會吸引更多關注,但是會誤導公眾,甚至影響媒體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設想。
三、考古——傳媒人才培養
1、考古——傳媒人才培養的目的及意義
根據傳播考古學的理念,媒體應該是其中的研究重點,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體界之間的交流機制,加強雙方的合作互動,特別是培養專業公眾考古傳播人才,成為其中的必備工作。本文認為公眾考古傳播人才培養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與媒體交流的公眾考古人員,第二部分是具備一定考古知識的媒體從業人員。二者都是選拔培養考古——傳媒復合型人才。傳媒人才是在大眾傳媒中以創造性勞動為社會和人類傳播事業做貢獻的一群人,所以公眾考古傳播人才的培養就可以認為是創造性探索公眾考古傳播模式的途徑,從而為完善公眾考古傳播機制提供基礎,所以需要考古和傳媒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
篇(3)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學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關于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考古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掘以及對發掘現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象而不去總結規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考古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展的規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發生。而我們現在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篇(4)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總體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總體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篇(5)
美術考古學的學術概念來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譯的《美術考古學發展史》首次將其引入到中國。之后,學術界并沒有關注學科定義、學科歸屬等方面的內容。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首次出現“美術考古學”的內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學》卷中也出現了“美術考古學”的詞條。在專著中明確為美術考古學作定義的是劉風君1995年出版的《美術考古學導論》和孫長初2004年出版的《中國藝術考古學初探》。不過,這些學科定義上的工作還只是停留于淺嘗輒止的層面上,并沒有專門的討論。
學科定義涉及學科的研究對象,同時,一個學科性質的準確認識,也需要涉及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通過學科之間的關系梳理,可以突出學科的特征,同時也可以完善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在關于美術考古學科關系的認識中,目前學者較多涉及的是與考古學、美術學、社會學、歷史學、圖像學等學科的關系,這其中涉及學科的本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的意義等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謂不廣、不可謂不具體。遺憾的是,在這些關系的討論中,基本上沒有考慮到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的特殊關系。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有相同之處,而且在研究資料的獲取上也有相同之處;同時,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響上也有相同之處。因此,我們提出美術考古的敘事特征和與宗教美術的學科關系作為理論深入的探討視角。
一、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敘事邏輯
這是一個關于敘事邏輯的學科定位問題。我們認為,美術考古如果作為分支學科看待,那么,從敘事邏輯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是美術學的二級學科。
首先,美術考古是將研究對象作為美術史現象來描述的。“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1](P5)是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在美術考古的研究過程中,這些美術遺跡和遺物轉化為美術發展史上的敘事遺存,圍繞美術遺跡和遺物展開的研究是關于構圖、造型、色彩和主題、風格、藝術進步等美術學科范疇的研究。以我國西域龜茲石窟為例,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它是關于石窟的考古對象;而在美術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藝術的研究對象,研究者是將它作為美術現象來研究的,學者們從龜茲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藝術影響。比如,希臘藝術的影響:“在龜茲石窟的早期壁畫中,人物顯得非常突出,與后期山水鳥獸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較大有明顯的不同,這就是受希臘以人為本藝術思想的表現。有些形象與希臘神話傳說似乎也有聯系,如克孜爾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獸身的金翅鳥,荷馬史詩中也有生動的描寫。被學術界所注目的龜茲壁畫,顯然也是有希臘藝術影響的痕跡。希臘藝術是推崇的,認為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龜茲藝術家接受了這樣的審美觀點,而且也對小乘佛教的禁欲主義給予了突破。”[2](P137)這些研究內容,已經完全是在美術學的學科范圍中進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藝術、漢畫像石墓葬藝術等,在進入美術考古視野后,都是作為美術發展史上的美術現象、敘事風格和藝術成就來研究的。
其次,考古學的學科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的研究趨勢。目前學術界中,不論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考古學學科還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美術學學科,學者們都希望美術考古擁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廣泛的研究領域,但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這種具有擴張性的發展要求。中國傳統的田野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標型學、器物形態學),這兩種方法都借鑒于自然科學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學是以物為研究標的的特性,這一基本點決定了田野考古學只能是“見物不見人”。美術考古如被作為田野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雖然研究對象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特殊對象——美術作品,但是它從屬于田野考古學的關系決定了其在方法論上必然是以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過程中強調過程的客觀性,禁止運用描述性語言,從而忽視了這種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觀性內容。有學者認為:“許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將考古發掘報告當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學科都離不開研究,否則就不是什么學問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語言也是錯誤的。”[3]在強調客觀性的制約下,美術考古歸于考古學缺少可操作性。
我們還可以從一些考古學前輩和權威性的觀點中得到旁證。比如,前輩夏鼐認為:“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標在于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這與美術史學者從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出發以研究各種美術品相比,則有原則性的差別;由于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在年代上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各歷史時代,所以它既屬于史前考古學的范圍,也屬于歷史考古學的范圍。又由于作為遺跡和遺物的各種美術品多是從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發現的,所以美術考古學與田野考古學的關系也相當密切!”[4](P9)目前,“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已經不能覆蓋美術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則成為一個重要的內容,我國目前美術考古取得的學科影響主要是在美術學領域。其一,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極大地豐富了美術史的研究內容。在美術考古發揮影響之前,我國美術史的研究依賴于傳世的美術作品和相關文獻,這些作品和文獻在傳播過程中指導創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產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動美術理論的發展。但是,在美術考古學科形成后,情況發生變化,大量的美術考古作品進入美術史的研究領域,不僅增加了傳統美術的作品數量,而且美術史的理論認識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術史教科書中,美術考古的內容已經進入到了所有朝代美術發展的認識中。其二,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術史研究模式。對于傳世美術作品的研究,美術史更多的是依靠傳統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論世的考釋,比如師承關系的梳理,等等。對于美術考古作品,考古學的地層學方法和類型學方法則被學者們熱情地引入,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理論也被學者們廣泛地運用,目前甚為流行的圖像學、敘事學等,皆為美術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提高了美術史研究的學術影響。這一點最好理解,美術考古將美術史的研究進入到石窟藝術、墓葬藝術、巖畫藝術等考古遺存的領域,美術史上的許多空白被填補,許多文化遺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術史在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因此,我們認為美術考古不應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作為美術學的分支學科。通過對美術考古定義的討論,我們提出一個求教大方的表述:美術考古是一門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在美術史層面上展開研究活動的美術學分支學科。
二、與宗教美術相關的敘事特征
這是一個從敘事特征角度討論學科關系的問題。
首先,從邏輯關系上對敘事特征的討論。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在概念上存在的關系是交叉關系。這樣的關系與全同關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對稱性和非傳遞性的性質。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學術界并沒有注意到它們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實際上,在它們的研究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與宗教信仰有關,同時,它們的研究對象基本上是通過考古手段獲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從敘事特征看,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因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墓葬藝術作品、石窟藝術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為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等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古建筑遺址、被掩埋的藝術作品等。這兩部分作品中,從目前的研究條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對象占有著極大的比重。這一現象,也與我國傳統文化的延承有關。自三代開始,人們就將與自然、先人有關的祭祀活動和與自己有關的埋葬活動作為了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以后的各類宗教思想發展不僅沒有降低這項活動的重要性,而且還從生命的價值、生命的不滅和生命的轉化等方面予以豐富和細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藝術活動之中,留下了豐富的美術作品。
宗教美術的研究對象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通過考古手段而獲得的美術作品,第二部分則是通過代代相傳的方式而保存、流傳的傳世作品。與美術考古一樣,宗教美術的第一部分占有極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與美術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疊,如墓葬藝術作品、石窟藝術作品等。這些美術作品都是通過考古的手段而獲得,這就使得這兩門學科有了更加緊密的學科關系,我們因此而可以提出這樣的關系命題:對于這部分作品,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是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活動。“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是主項,“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活動”是謂項,主項之間的關系是對稱性的性質。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所具有的對稱性關系,雖然是有條件的,不能覆蓋兩學科的所有內容,但是考慮到這部分重疊的內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這部分作品中優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這樣的對稱性關系使得兩學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別的意義。在建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的關系命題之后,我們就可以從許多共同性的方面來深入思考它們的學科性質了。
其次,關于美術作品埋葬方式的敘事認識。
在通過考古手段而獲得的美術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無疑問是美術作品完成敘事的重要內容,可是這一點目前沒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的研究論文中,研究對象的確定常常是側重于從作品的發現角度來認識的,即考古學的角度。我們則認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這是一個關于作品本體的角度。當然,作品埋葬和作品發現都是屬于作品存在的范疇,作品發現也已經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況,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種直接性的觀察,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收集和反映相關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傳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個主動的行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觀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實現;而作品的發現,則可能是一個被動的行為,其中的一些環節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預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與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沒有關系的,極端情況下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發現不考慮這些因素,那么認識原作品所有人的創作就有了一個信息損失、甚至歪曲的可能。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比如漢墓壁畫,墓主人將反映自己社會地位、日常生活和對另一個世界想象的繪畫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現自己的長生思想。對他而言,長生思想的表現是一個長生行為,是對長生信仰的體驗,同時,這一定是一個個人的行動。他絕對沒有考慮到這樣的現象:考古學的發掘活動,發現了他的行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說,墓主人墓葬繪畫行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內容,另外的內容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內容和后人的內容之間的敘事結構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時,也可能會因為敘事結構的轉化而損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誤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與作品的發現,是一個存在一定意義差別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作品為什么存在?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作品,其創作是在信仰的指導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個人的魂魄并不隨著自己的生命結束而結束,而是在另一個世界能夠繼續,所以他要為那個世界的存在而作這個世界的準備,因此他的行為就涉及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的研究對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術作品。這樣的美術作品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專門創作而直接參加宗教行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畫;一種是之前創作而間接參加宗教行為的作品,如墓葬藝術中的一些帛畫、雕塑、冥器等作品。這兩類作品就創作過程而言,有著不同的創作性質,第一種是宗教行為性質的創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導下進行,為宗教體驗服務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種是世俗行為性質的創作,在創作過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導。這兩類作品能夠有敘事上的同構,是因為埋葬活動提供了條件,為宗教信仰服務是作品完成整個敘事過程之后才得到的創作意義。這兩類作品在考古學的活動中,都是以歷史遺存的形式出現,就作品的發現而言,它們是以相同形式的遺存出現的,它們的主題也都是為墓主人或供養人的宗教信仰服務的創作行為。但是,宗教行為的創作行為和世俗行為的創作行為是存在著區別的,世俗行為成為宗教行為必須有一個結構演變的過程。
從邏輯關系角度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有著部分對稱性的關系,其意義是肯定兩學科的共同性,從共同性的角度出發認識它們的優秀作品;而從埋葬角度出發,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被考慮的則是兩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當然,這個差異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開的,目的是從兩學科的關系層面上思考學科性質。但是,如果我們在了解、分析埋葬美術作品時沒有考慮到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學科之間的差異,那我們的認識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錯誤的。
再次,關于敘事意義的理論認識。
敘事作品是一個動態的意義生成系統。[5]通過學科邏輯關系的認識,我們可以從邏輯角度認識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所存在的共同性;通過作品埋葬角度的認識,我們可以從作品存在的角度認識兩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同時,兩學科的結合思考還可以在操作層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論意義。這個意義,就是在認識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學科特征的基礎上突出兩者結合思考后的指導意義,即強調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所具有的敘事意義。
其一,敘事主題的單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中,敘事的結構往往都顯得非常宏大,幾乎所有的構圖都試圖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間和世外,這是宗教信仰指導的必然結果。如我國最早的黃帝圖像就出現在山東武梁祠的畫像石中,與他同時出現的還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們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圖像,墓主人用這樣的構圖說明西王母對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對西王母無所不及的期待。無所不及是一個多么大的結構,墓主人能夠在有限的畫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條件下完成這樣大的結構嗎?顯然這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術可以很輕松和很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敘事主題的單一,或敘事主題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術作品中,作品的主體都是至上神或主宰這個世界的神靈。在構圖上,這個主體占據著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國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體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單一的形象反映豐富的世界,在世俗美術創作中是非常難辦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藝術創作規律,但是這在宗教美術創作中卻是普遍的現象。在宗教美術創作中,至上神與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現的是終極關懷,藝術審美感來自信仰經驗。如此,凈化的世界也同時產生了簡化的世界,敘事主題自然就顯得單一,顯得集中。當美術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術的范疇時,相關的敘事同樣是沿著這樣的路徑進行的,豐富的世界可以作為創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題是單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術作品的敘事主題單一、集中的特點,可以充分反映、同時也充分論證了宗教行為的性質和影響的存在。
其二,情節的真實性。
宗教美術是描寫另一個世界的,與現實世界對照,它是不真實的。但是,宗教美術作品能夠存在的理由卻是來自于宗教經驗,即這些作品的內容是真實的。這樣的真實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現了情節的真實性。情節的真實性當然是來自于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宗教經驗對這樣的真實是支持的態度。宗教美術作品的構圖體現著這樣的“真實性”。在我國神話傳說中,女媧是一個大神,有著極高的地位。我國早期的歷史書籍中,幾乎都有關于女媧的文字記載,在各地的民間傳說中,女媧也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料。關于女媧神話的發展,學者們的研究是將女媧的神格分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兩大類。為什么女媧在這兩方面作出貢獻?因為她是女神,這一點充分表現在藝術形象中。她能夠如現實世界中的女性一樣造人,而且她有著許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種造人法,即化生人類、摶土作人和孕育人類[6](P29)。就神話的流傳而言,女媧的這些情節都是真實的。漢畫像石中,女媧所擁有的與生育有關的情節也是真實的。在漢畫像石里,女媧的形象一般被描寫為人首蛇身狀,有著非常濃郁的原始氣息。因為在原始社會,女性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動物,生育力特別強,女媧蛇身就有了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話中,蛇的生育本領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話里,許多造物的大神因為本領大、功勞大而與蛇產生聯系。在造物的神話人物中,燭龍是個大神,他就有著蛇的形態。
因此,在宗教美術和美術考古的作品中,情節的真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敘事特征,這一點與世俗美術有相似的地方,但它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即宗教美術并不是依靠寫實來達到真實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張來達到真實的,更多的依靠聯想,依靠聯想來獲得情節的真實,聯系最直接的說明,就是物象的符號化。
其三,物象的符號化。
在宗教美術作品中,物象符號化的手法無處不在,每一個物象都拒絕隨意的理解,必須從某一個已經存在的特定的概念來入手,從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義。一是因為宗教美術有著強大的象征體系,天邊的云氣是象征仙界的符號,飛翔的鳥是象征使者的符號,地面行走的神獸是象征宗教行為某個過程的符號,每一個物象都與象征體系有著對應的關系,有了符號化的運用,物象的意義不僅更加明確,而且接受也有了流暢的表達過程;另一個原因是宗教美術所包含的宗教儀式內容,儀式支持宗教美術,但對藝術創作有約束的要求,這個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過符號的聯系來實現,這樣的聯系在宗教的象征體系中就產生了藝術的聯想。當然,我們也同時注意到,世俗與宗教有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體系,所以宗教物象與世俗物象是有區別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體系中,它是長生的物象,使信徒聯想到與長生有關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與嫦娥有了聯系。特別是在漢代,畫像石中有將嫦娥與蟾蜍聯系在一起構圖的現象,而且這種圖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為形象的問題,嫦娥和蟾蜍是被分開的。如白居易的《蝦蟆》詩,不僅對嫦娥與蟾蜍作了區別,而且還特別提出害怕將蝦蟆拿來聯系嫦娥,認為這樣會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飛上天,跳遠隨妲娥。往往蝕明月,譴君無奈何!”因此,物象的符號化不僅反映出宗教美術的敘事路徑,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說明宗教美術區別于世俗美術的藝術特征。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就學科性質的認識而言,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存在的關系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命題,這兩門學科的共性可以使我們在認識學科性質上尋找到諸如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邏輯關系,特別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響上所存在的相同敘事結構,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的學科定位。
[參考文獻]
[1]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榮春,主編.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M].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4.
[3]朱滸.全國首屆藝術考古學理論研討會會議綜述[J].中國美術研究,2007,(3).
篇(6)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41-02
一、書名及作者簡介
書名:《民族文物通論》,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遼寧省遼陽市,是我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首席顧問,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長期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研究,側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遠古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巫與巫術》、《中國生育信仰》、《中國民間神像》、《中國民族文物通論》、《共妻制與共夫制》、《女兒國親歷記》等。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的“南汪北宋”兩位考古學者,其中的“汪”指汪寧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蘇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師,這樣的評價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考古問題的學術方向,同時也是對他的一種鞭策。宋先生一直把這句評價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二、內容概要
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方法問題,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點,田野調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與方法,民族考古問題,民族文物鑒定,民族文物的應用等。
第二部分為具體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豐富多彩,種類繁多,作者選擇了若干典型個例,與考古遺物對比,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綜合性研究,不僅介紹了若干研究方法,也進一步闡述了民族文物的價值。
第三部分為古代民族風俗畫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書中選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風俗畫,加以剖析,對民族文物研究和鑒定有重要借鑒。
由于時間關系與精力所限,筆者僅選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進行一些淺顯的歸納與總結,全書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論方法為基礎,輔以第二部分的具體事例,系統地論述了民族文物的相關理論,筆者也從具體事例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方法的理性認識。筆者認為通過這兩部分的概述與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內容與內在精神。作者在闡述民族文物理論時,詳以事例,并構建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論體系,為民族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
三、書中經典
(一)民族文物定義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爭論較多。作者認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產生以來,各民族所創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歷史階段、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態形象,看得見,摸得著,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內涵,這正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特色。具體來說,民族文物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從民族產生至今各族所遺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包括考古發掘品、傳世文物和近現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來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對民族文物做了較為全面客觀的定義,使民族文物從空間與時間上與現在相連接,并有所區別。不僅總結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獨特的特點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等,而且歸納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獨具的特點: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層保護,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損壞;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為無機物,近代民族文物則以有機物質為主,文物保護難度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結構完整、功能明確,還有種種傳說;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為國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人所有,這給文物征集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方法
1.民族文物應該有自己的層次學。作者從自己所學考古學的背景出發,把相應的理念與構想帶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據民族文物的特點,提出民族文物層次學。如果比較而言,考古學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無誤的遞呈關系,下早上晚。考古學家可根據地層關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遺物進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沒有地層的堆積和保護,干擾嚴重,古今摻雜,而且本身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無序性或紊亂性,關系錯綜復雜。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學那樣按地層發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把無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來,弄清來龍去脈,找出時間、空間序列,也就是分清歷史層次,各就其位,還原其本來的歷史坐標。
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種民族文物層次學,作為指導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論之一。其中應包括下列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標準文物,作為鑒選有關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時代的同類文物,又有發展演變規律,運用這些規律也可以鑒別同一時期的有關文物。這樣就可以把堆積一處的眾多民族文物按時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確其時間性,這一點在工具、器皿、服裝、工藝品等方面都很實用,能找出它們的層次關系。
民族文物層次學,使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來,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坐標――時間階段與空間位置,這對現階段的民族博物館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該建立民族支系學。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民族支系學,用以明確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對民族文物的細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而且不少民族內部又分許多支系,反映在物質文化或文物制度上當然也千差萬別。我們在處理民族文物時首先應該確認屬于某種民族,即確定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礎。其次為了區別出民族支系、地區,必須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區分別開來。
以清代云南彝族為例,即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等支系,每個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質文化特點,其文物是不一樣的。類似問題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民族內部的支系,不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區、語言、文物上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作者認為民族支系學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建立民族支系學理論體系,還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屬的全貌。
民族支系學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淵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語言特點、分布區域及其演變,本支系與其他支系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異同。從中得出的理論原則,必然會深化民族史、民族學研究,有助于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說民族文物層次學是解決民族文物發展系列的準則,那么民族支系學則是解決民族間、民族內部支系間關系的重要理論準則。
任何一個民族支系的確定,都應該歸納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學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具體地說,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時間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既是該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們與其他支系相區別的地方。以海南黎族為例,其包括五個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個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樣的,語言也有一定差別,當然在文身的圖案上也有一定差別。
四、存留問題的淺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書中針對民族文物的分類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產工具、舟車、手工工藝、宗教文物與文字。筆者認為還應包括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構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為從分類的內容來看,作者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關“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論述了民族文物與考古的問題,客觀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較研究與民族考古學混為一談。
其次,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應該是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國75屆人類學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考古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關系”。也說明它是兩種學科的結合,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不難看出,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是以考古學為主,民族學只是它的一種研究手段,所以應該突出考古學。最后,作者認為所謂民族考古學并不具備一種學科的特征。
由于學科是指學術研究部門的分類,每種學科的確立,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和任務,但是民族考古學并沒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對象,所研究的課題都是考古學的內容,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作者認為,他們做的,只是把民族學方法、資料引進考古學而已。
綜上所述,民族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只是多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還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學科――“民族考古學”。
篇(7)
根據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對“原史(Protohistory)”的定義,原史的時間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記錄歷史”出現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義原史時代是“緊接著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書寫文件證明的歷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將“原史時代”的時間段界定于史前與歷史兩大階段的過度階段。
作為一個主要使用于考古學上的詞語,Christopher Hawkes對“原史時代”加以解釋認為,原史的概念是相對于文獻豐富的歷史,這一時期已經有一些文書記錄,但是這些記錄只是一些片斷,涉及社會非常少的方面,這些記錄可能表現于一些刻銘、硬幣等等,或是其他地區散亂的文本資料。[2] Glyn Daniel則認為“原史時期”一詞,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的時期。[3]在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中,認為所謂“原史”或“原始史”的涵義是,“首先具有一種方法論之意義,應用于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的文化群體。為了研究它們,人們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擁有文字、然而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所記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盧人,他們為希臘與拉丁作家所記述);也可以指那些通過後世的口頭傳說、記憶或者記載而保存下來其歷史的人群。在此兩種狀況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學資料及間接的文字記載資料兩方面。此時期在年代學體系中只具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范圍,而且也不精確。”[4]也曾有人這么總結原史時代的特點:在最初書寫文獻還很稀少,并且很難讀懂,多數最初的記錄還沒有完全的破譯。這歷史的最初階段通常被稱之為原史時代。後世的學者也會對這個時代的歷史不斷的進行文書上的補充。這些文獻,在結合考古資料之後,也會成為值得重視的材料。好比說一個傳說中的國王的名字被發現在刻銘上,關于這個國王的記載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來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較原始的狀態,是一種“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語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島語)指的是南島語的一種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與Austronesian 的差別,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狀態。同樣的,我們將先商稱為“Proto Shang”、將先周稱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經存在,所以我們不會將先商稱為“pre-Shang”,也不會將先周稱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這個階段里,史學開始萌芽,一些記錄開始以各種形式出現,雖有文書記錄,但是仍不足以讓我們據之復原歷史,這一階段有別于史前,也有別于歷史時期,是史前向歷史時期發展的一個過度階段。在對這一階段進行研究時,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等學科綜合起來的一種研究。
雖然,作為方法論的“原史”的概念還沒有被更深入的定義、討論,對于其意涵還有不太相同的認識,但是“原史時代”在西方已經是受到普遍承認的了。綜上,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總結出幾條基本原則:1.原史時代是介于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2.原史時代研究的對象應是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文化群體;3. 由于原史時代當代的文獻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4.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以下,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來檢驗中國原史時代是否存在。
對“中國原史時代”的界定
過去我們一般將古史分為史前、歷史兩大階段或是史前、傳說、信史三大階段。這兩種分類都是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材料出發的。在考古學引入中國之後,史料的范圍已經由文字材料擴大到包括文獻(當時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獲取方法是考古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對中國先秦史的研究(這里指的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商周階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統一中國(221B.C.))。張光直先生即曾說過,“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現越積越多,越多便出現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考古學還發掘出新的文字材料來,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果,是知道了傳統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6]
戰國以前同時期的傳世文獻材料非常少,即使是當時流傳下來的,如尚書、周易、詩經等等的文獻材料里,也有許多後人補作或是經傳抄而改變的內容。後世對這一時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東周及漢代,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實情況外,大多是為了時代需要加以改編、附會而成。所以,我們在面對傳世文獻以及通過這些文獻而認識的古史時,總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態度。即使是現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證的《史記.周本記》,其所能為我們提供的,也只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一個框架,還須要我們透過其他手段進行復原。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史學傳統肇始于西周王室覆滅「王官之學降于民,知識分子才脫離王室的束縛,逐漸由過去的“巫”史中走出來。晉《乘》、楚《檮杌》、魯史《春秋》,都成于這個時期。今日我們讀到的《左氏春秋》,開創編年記事的體例,是中國歷史學發展成熟的標志。至此,可供後世學者研究的確實的文獻史料開始豐富,文獻材料為學者提供了全方位更為豐富的論證材料,考古學成果成為歷史文獻的一種參照或是補充,而非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如此才算是進入真正的「歷史階段。
王樹民先生指出,現在有些人對于古代史學和史料不加分別,以為根據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說明當時的史學了,正與把傳說當作史實同樣是不正確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遺物,史料價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況下,也可能為史官所作,但原為占卜之用,不是歷史記載。鐘鼎文多為周代之物,記載了許多重要的史實,但原為紀念性質,也不是歷史記載。[7]所以,不論是由史料或是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三代時期的研究是有其獨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
由現存的文獻材料來檢視中國(中原地區)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戰國以前)的傳世文獻里沒有比較全面的史學著作,所見可靠的文獻材料也多經後人修改。考古發現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但是這些文字表現的是歷法、卜筮、紀念,或是簡單記事文字,只表現了商周王朝片段的歷史,雖然已經極具歷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現當時歷史的方方面面。雖然已經有了史官,但是當時的史官是為上層及祭祀占卜服務,其性質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職。“史”的概念還在萌芽的階段,真正為記錄歷史的歷史記錄還沒出現。這些都與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相符,所以,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商、西周時期(甚至是春秋時期)作為中國的原史時代。李學勤先生即根據Glyn Daniel對原史時代的定義認為,東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經脫離了這種“原史時期”而跨入真正意義的“歷史時期”了[8]。此外,作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但是仍有相當的文獻材料及考古線索)夏、先商、先周也應屬於中國的原史時代重要的一部分。這牽涉的不僅是時間的概念,更是一種族及考古學文化發展的概念。因而在尋找夏的根源上,我們更應該將著眼點放在晚期龍山文化。至於繁複龐大的傳說記載,由於其涉及的時間范圍太長,似乎不宜將所有的傳說都歸入原史時代范圍;此外,多數傳說內容也很難與考古材料相結合,即使是距離夏代較近的“三皇五帝”傳說也很難落實在考古材料上,所以這里不把過去所謂的“傳說時代”等同于原史時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種概念及材料。
中國的原史時代,及其與傳統中國上古史的區別在于,傳統史學由文獻出發,以政治時間作為歷史分期的標準,所以一般將秦以前劃為上古史的范圍。在過去所認為無文字的史前時代以及文字發明之後的歷史時代之間加入一個“原史時代”所表現的是歷史學的一種初興狀態,以及我們對這一階段的歷史進行研究時所面對的史料的多樣性(與史前及文獻發達時期相較)。這里所指稱的“中國原史時代”是,一時代的歷史由傳說或是不充分的文獻記述,必須通過考古材料對這些傳說或文獻加以檢驗確定其正確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資料建立、補充文獻所缺乏的各種對當時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現的也只是當時社會的極小的一個部分)。這一階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等等一起建構出當時的歷史、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而這種對“原史時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學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之下才有可能展開。
所以,原史時代概念的提出不論是對歷史學研究或是考古學研究都是有所幫助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對象并不應該被限定在整個現代中國領土的范圍,而是著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為以中原華夏民族的原史時代為中心,其范圍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傳世文獻、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向外輻射至與之相關的各個地區、族群、文化(當然,如果該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視為認定其族屬、文化以及認定其與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將中國原史時代表現為一個各種活動、族群聯系在一起的有機體。而對于現代中國境內曾經有的各個族群、文化的原史時代的研究,則應該將其分別命名(如:匈奴原史時代、女真原史時代等等),成為以其為主體的原史時代,以求與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原史時代區隔開來。
所以,中國的原史時代是:1.時間段在文獻所記載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為中心,兼及在各種方面與原史時代的中原有聯繫的各種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為當代及後世文獻,以及原史時代的古文字、考古遺跡遺物、傳世文物等等;4.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中國原史考古
中國原史時代的定義已如上述,而作為中國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環的中國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歷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獻材料對考古產生的不同影響。史前考古沒有當代的文獻材料,後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神話為非客觀的記述,本來無法作為有效的根據。傳說的核心部分固然為古代實有,與後人因想象而虛構的不同,但是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不僅時間、地點、人物易發生錯亂,更容易混入神話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性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而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并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原史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學材料在許多模糊的歷史問題的研究上具有的決定性的影響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原史為中心,輻及與之有關的各個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沒有文字,雖然其族屬的確認主要是依據古文字、文獻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學文化被認識的基礎之上,進行文化因素分析,我們不但可以加強認識中原文化與相關族群之間的關系,更可以建構出以某一族群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間的復雜關系。
而中原地區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學以及古文字、文獻記載三種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與考古學相關的各種課題外,還可以在文字資料的幫助下,建立中國原史的年表,并結合古文字、文獻記載的時間、人物、事件、地點,復原出一種將考古學文化與史實相結合的中國原史時代。
參考文獻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處轉引自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處轉引自劉文鎖:《論史前、原史及歷史時期的概念》,《華夏考古》1998年3期,93頁)。
[5] 見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9月。
篇(8)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識社會學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國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題思想豐富,充滿著與傳統不相銜接且存在于認識本身的“斷裂”,也就是說,他認為傳統的知識系譜學失去了連續性。愉悅、瘋癲、監獄、犯罪、性、醫學、文學、審美、人文科學誕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題,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這些研究在《福柯》一書中總結為三個主題詞:知識(savoir)、權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脈絡如同他對歷史的看法一樣,總是存在著非連續性――如歷史并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具有決定論的特征,這些非連續性不僅體現于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如瘋癲、權力等),而且也體現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學),就是在這些非連續性和多元歷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構建了對知識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認識地形圖。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廣泛和富有見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諸多學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以下簡稱《詞與物》)是米歇爾?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學三部曲(其他為1963年出版的《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和1969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之一。福柯的考古學既不是指一門學科,也不是要構建一種傳統的連續的線性歷史,而是一個研究領域,展示某種學科話語在一定時期產生的可能條件,呈現把不同話語事件(局部知識)和權力聯系起來的機制的橫向截面圖。福柯認為,話語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變化,他把這些條件稱作“認識型”(épistémè),理解“認識型”是理解考古學方法的關鍵。這里的話語有別于語言學的概念,是指從屬于不同領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規則的一攬子陳述。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書――被認為是自己《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兩本書的附記――卻使他名聲鵲起,享有了國際聲望。自《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初,福柯認為自己的“橫向上”考古學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轉向了“縱向上”系譜學研究。由“考古學”轉向“系譜學”,其目的在于強調,在橫向閱讀話語性(即橫切面構型研究)之外,還存在著縱向閱讀我們話語體制的歷史決定的必要性。從考古學向系譜學的轉向表現為研究關鍵詞從“認識型”向“裝置”(dispositif)概念的轉換,即從“不同理論和辯論生成的可能條件”或“特定話語的裝置”向“權力的運作裝置”或“所有非話語社會活動”的轉換,從“研究話語對象”轉向了“非話語現實的實踐、策略、機構”等。由此福柯從橫向上對話語生成條件的考察轉向了縱向上的對知識與權力關系的考察。這種轉換是在“認識型”認識上的過渡和延伸,“裝置是一種比認識型更普遍的情況。或者說,認識型是一種特殊的話語裝置,它與裝置的區別在于,后者既是話語又是非話語的,它的構成元素更為混雜與復雜”[1]300。
如果考古學是對某一既定時期“知識”(savoir) 法語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譯為“知識”。在學界,福柯的savoir經常被翻譯為“知識”。福柯對兩者做了區分: connaissances與有關可認識對象的話語的構成相對應,也就是說,一種獨立于認識主體的、對客體進行合理化、辨認和分類的復雜過程;相反, savoir指認識主體在認識過程中的變化和修正過程,簡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關不同客體話語的構成,savoir是描述認識(connatre)主體在認識中的變化過程。 話語現條件(政治的、經濟的、哲學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譜學則偏重從多元性、發散、偶然的開始出發,試圖重構知識(savoir)與認識對象(客體化)及認識主體(主體化)發生關系的方法。換句話說,知識與權力構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們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學和系譜學不是去構建一個傳統的、連續的思想或觀念史。“在寫《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時候,我認為自己正在書寫科學的歷史。”然而,在《詞與物》中,他認為:“在科學的傳統史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方法:不是過多地去考慮科學的內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種探究社會事實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學實踐有一個歷史顯露過程,它包含著歷史性的存在和發展,遵循著一定數量與其內容無關的演變路徑。必須把科學的內容和組織形式問題放在一邊,來研究科學存在或一種既定科學開始存在并在社會中承擔一定數量功能的原因。這就是我在《知識考古學》中試圖界定的觀點。”[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史學特征,而且顯示了考古學主題的一致性。
考古學和系譜學分析構成了福柯研究知識、權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從系譜學出發,福柯認為存在著三種系譜學可能領域:我們自己與真理發生關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認識主體;與權力領域發生關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影響他者的主體;與道德領域發生聯系的歷史本體論,使我們構建成倫理行動者。如,《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這三者都存在,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更多涉及真理,《規訓與懲罰》涉及權力,《性史》涉及道德[3]。這種本體論與其說是在分析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性,倒不如說是在探討有關某種歷史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屬于分析歷史哲學的范疇。可以說,福柯的考古學和系譜學分析構建了一個橫向和縱向交叉的(客體化與主體化)知識、權力與自我研究的立體圖景。但就《詞與物》而言,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某種社會文化現實或知識的方法,盡管這些現實或知識在縱向層面上與權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了知識生成條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識理解格柵
“知識”(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詞。自《古典時代的瘋癲史》(1961年)和《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1963年)開始,他就在探求一種知識(savoir)與形成該知識的社會、經濟、歷史等條件間的關系。福柯的《詞與物》仍是在橫向維度上來思考不同科學間的關系。他的這部著作就是試圖去回答《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視角考古學》中已經提出的問題: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無直接溝通的科學實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根據相同形式、朝著相同方向同時發生的嬗變(transformations),這是認識論層面上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與欲望、需求和沖動可以表現在個體的話語及其行為之中不同,作為一種科學出現、發展和發揮作用的語境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科學中并不表現為科學話語的形式。換句話說,非話語組成(如經濟和社會條件)與話語組成(formations)內容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和純粹的“表達”(expressif)關系,這是考古學層面上的問題[2]160161。具體地說,在第一個問題中,福柯選擇了三個不同的、彼此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領域:語法、自然歷史和財富分析,藉此展示它們在兩個時期(17世紀中期和18世紀中期)所發生的一攬子相似的變遷,指出了知識圍繞并進行組織的三種“認識型”原則:相似性、表象和歷史性。在第二個問題中,他從考古學分析入手,試圖從這些科學構建自己對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認識主體相對該對象領域的定位方法的層面上來理解語法、自然歷史、財富分析的變遷。
福柯的 “人文科學考古學”的中心問題是“從何時開始人成為知識的對象”,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向讀者展現了在西方社會不同時期存在著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認識構型。具體地說,福柯的《詞與物》試圖借助三種科學實踐變遷(從“普通語法”到“語言學”,從“自然歷史”到“生物學”,從“財富分析”到“政治經濟學”)的比較來展示一種“認識型”的嬗變歷史,“認識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論和辯論的可能發生條件,是知識(savoir)的“歷史的先驗”或“認識場域”。在福柯看來,“在一個社會中,知識(connaissances)、哲學思想、日常觀點以及機構、商業與治安實踐、風俗習慣等,都指向一定的內在于這個社會的知識(savoir)。這種知識與在科學書籍、哲學理論、宗教辯護等中找到的知識(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這種知識(savoir)使一種理論、一種觀點或實踐成為可能”[4]498。換句話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場域”或“認識型”,它是不同知識(connaissances)產生的基礎,并影響著它們的出現。找出“認識型”就是要去發現一種“真理”――一套能夠在每時每刻讓每個人發表被看作是“真實的”(vrais)陳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體驗。
福柯認為,自古典時代以來,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現了兩次重要的認識型間斷性:“第一個間斷性開創了古典時代(大致在17世紀中葉),而第二個間斷性則在19世紀初,標志著我們的現代性的開始。” [5]13在這兩個間斷中,福柯明確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種認識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認識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異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時代的認識型,最后是現代認識型。在現代認識型中,生命、工作和語言成了研究的對象,歷史性則是現代認識型的組織參照。人們從自然歷史過渡到了生物學,從財富分析過渡到了經濟學,從語法過渡到了語言學。在這些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認識對象:在經濟學方面,生產代替了交換;在生物學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體;在語文學方面,語言代替了話語。科學改變了性質和形式,前后之間存在著斷裂。
“在時至16世紀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識(savoir)中起著構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導文本的評注和闡釋;相似性組織著符號規則,使可見與不可見的物的認識成為可能,引導著表達藝術。”[5]32在文藝復興時期,相似性主要通過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類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戰勝了時間和空間,存在與其自身的根本關系是相似性的關系,相似性成了知識的組織原則。古典時代(17和18世紀),問題在于創造一個符號系統,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構合在一起來產生一種秩序。古典時期的認識型是通過普遍度量科學(mathesis)、分類學(taxinomia)和發生學(genèse)構合的系統來界定的,換句話說,這三個概念界定了古典時代知識(savoir)的普通構型。也就是說,在17和18世紀,普遍度量科學、分類學和發生學通過圖表(tableau)來表達知識,根據一致性和差異性來組織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實的存在變得可見)被秩序化于圖表,圖表成了知識(savoir)的中心,自然的歷史、語法以及貨幣科學就存在于這個圖表之中。
進入現代后,一致性的圖表開始解體,圖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場所、所有關系的發源地,知識寄存于一個新的空間、存在于歷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換句話說,在19世紀,知識的構成不再基于圖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鏈接(enchanement)和變遷(devenir),這種變遷的流變被吸取在人類學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對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圖表,而是一種有關人這種經驗個體的秩序現象,這種秩序現在從屬于物本身及其內部法則。用福柯的話說:“在這種(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顯示的對象,其顯示的是它們與人這種存在所建立的關系。這種擁有自我存在和表達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現于生命體、交換物體以及詞所騰出的空間中。生命體、交換物和詞放棄自己時至當時仍是其自然場所的表象,退縮回物的深處,根據生命、生產和語言法則回歸到自身。” [5]324也就是說,物回歸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約束中,語言及其歷史、生命及其組織和自治、勞動及其生產能力就這樣出現了。面對這種情況,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語言”留下的空間中形成了人,一個既生活、說話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說話和工作中被認識的人,即伴隨被定義話語的古典語言停止了對經驗世界的立法作用,人開始出現在19世紀。也就是在生活、語言和工作的自身回歸中,出現了人的實證性并成了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
自康德以來,人的經驗―超驗雙重特性使人文科學具有了獨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認識的主體又成了認識的客體,實現了自己的主體化和客體化。“現代思想中的所建構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著雙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實證性的基礎,而且以一種不能說是特權的方式存在于經驗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當人們決定把人當作科學對象時,人文科學還沒有出現,只有當人必須被思考和認識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時才出現了人文科學。“一般說來,人之所以成為人文科學研究對象,不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形式,而是這種生命體在自己從屬其中的生活內部構建因之而進行生活的表達,從該表達出發,人具有了表達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學實際在生活、講話和生產層面上來研究人。”[5]356人文科學不是對“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對“在實證性(鮮活的存在、勞動、說話)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該存在能夠知道“什么是生命”、“勞動及其法則意味著什么”,以及“用何種方法進行說話”等的分析[5]364。不過隨著后現代主義先驅的尼采(1844―1900)的“誰在講話”的提問和馬拉美(1842―1898)的 “詞在講話”的回答,在福柯看來,作為實證性的人因語言話語地位的回復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畫在“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被海水抹去了一樣。
這兩個重要的間斷反映了“認識型”或人文科學產生的可能條件的嬗變,換言之,不同時代的知識(connaissances)的生產有著不同的“認識型”,即不同的知識發生的可能條件,或者說,詞與物(或能指與所指)間的構合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話語實踐”格柵――在這里,話語實踐被界定為:“一系列無名的、歷史的、常常在既定時空中被確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在某個既定時期,為某給定社會、經濟、地理、語言等領域規定了陳述功能發揮作用的條件。”[5]153154
三、從象征走向現實:格柵的意義
《詞與物》的原名為《物之序》,在編輯的要求下才改成《詞與物》。《詞與物》中的秩序(ordre)是與認識型、歷史的先驗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為物的內部規律和彼此借以審視的秘密網絡而產生于物中的東西,又是只通過一種視角、關注和語言格柵才得以存在的東西;就只是在這種空白網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現出來,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靜靜地等待著自己被陳述出來的時刻。”[5]153154尋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體驗,就是“從去重新發現知識(connnaissances)和理論依據什么才成為可能;知識依據何種秩序空間才得以構成;基于何種歷史先驗、在何種實證性的元素中,觀念才得以出現、科學得以形成”[5]13的過程。從書中看到,所謂的“物之序”意味著按不同的“認識型”或 “歷史先驗 ”對物進行秩序化表述:文藝復興時期按相似性組織的物之序,在古典時代通過依據差異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圖表秩序,現代時期則因歷史性而依據變遷途徑等形成了19世紀的物之序。
總之,福柯的《詞與物》體現三種知識的組織中心:文藝復興時期的“上帝”,古典時代的“理性”(無限性)與現代時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語言將成為“知識”圍繞組織的中心而引發的人的消失。實際上,福柯的“認識型”演變也反映著西方哲學自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發展路徑:神學、理性主義、有限理性、語言學轉向。
就《詞與物》的分析來看,福柯的研究一開始就表現為對作為唯我論的、非歷史性的、自我構建的、絕對自由意識的大寫主體的批判――在福柯看來,從笛卡爾到薩特以來的法國哲學中的主體意識成了為萬物立法的尺度。他從“人之死”中來探討西方文化中知識的形成,即不參照主體地來探討知識、話語、對象領域等的形成,主體和客體都被看作構建于外部決定性基礎上的對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來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體之死,作為大寫知識、大寫自由、大寫語言和大寫歷史來源與根本的大寫主體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學只需要進行筆錄,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識、大寫的我和大寫的主體。在這種今天撼動我們的喧囂中,必須要認識到一個世界的誕生, 在那里,我們知道主體不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賴性,也不是絕對的本源,而是不斷地進行修正的函數”[4]788789。在這里,福柯解構了西方文化中有關人的無限性描述和大寫理性,于是歷史不再是線性的、連續的歷史,不再是不斷完善的進步,歷史變成了復數,一種出現于不同實證元素中的歷史叉。非連續、偶然、獨特性成了福柯描述歷史的特征,正是這些特征體現著西方文化“認識場域”的變遷。換句話說,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變遷,也正是這些特征成了我們理解福柯的知識、權力和自我的閱讀格柵。
雖然《詞與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們對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豐富、晦澀難懂和難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語言間的可譯阻止了人們進一步深入理解的熱情。雖然福柯在當時的法國因自己的思想發生了許多論戰,但我們無意去評判社會人文科學領域中的是非,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學之社會學”概念已經對我們有所啟發――社會學研究有著自己的不同語境。不過從經驗角度來講,研讀《詞與物》具有重要的現實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理論方面,一方面,《詞與物》提出的非連續歷史觀豐富了對歷史哲學的理解,為人們提供了理解歷史的新視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歷史觀既是一種歷史本體論,又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另一方面,特別是, 《詞與物》中提出的“認識型”概念如同托馬斯?庫恩的“范式”一樣,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知識變遷的框架,一種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識變遷的框架(不過這不是一種結構主義的描述),一種構合能指(詞)與所指(物)的認識格柵。
在實踐方面。一方面,在進行史學著述時,它能促使我們從不同視角和方法來思考歷史的發展和歷史的撰寫;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說:“支配一種文化的語言、知覺圖式、交流、技術、價值、實踐體系等的基本代碼,從一開始就為每個人確定了與其相關并置身其中的經驗秩序。”[5]11
福柯不斷地提醒讀者自己《詞與物》的研究語境是西方文化與西方社會,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認識場域”的變遷。這種知識社會學的啟發性意義在于,不同時代和社會存在著解讀當時知識生產的理解格柵。因此,理解福柯的“認識型”不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會的知識變遷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領會中國語境下的知識生產精神。它使我們認識到,知識的生產因歷史背景不同,會產生知識形成方式上的差異,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詞”因“話語實踐”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話語實踐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認識型”變遷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認識歷史的非連續性和不同時代知識(connaissances)有著不同的認識邏輯或文化編碼特征,話語實踐是理解能指與所指間意義指稱過程的關鍵。這種實踐的必要性在于當前的發展勢頭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趨勢以及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與轉型。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傳播的全球化。在傳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過程中,文化間的彼此認識和融合成為必要和必然的趨勢。在本土層面上,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僅體現為主體及其表達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傳播來構建一種適合“和諧社會”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這都需要理解相關知識的生產與組織原則,而福柯的“認識型”則為這種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啟發。總體來說,這種隱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識組織原則,對文化自身的生產以及不同文化間的彼此理解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參考文獻: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篇(9)
從大約公元1000年起,馬紹那人就一直居住在大津巴布韋一帶,他們是牧民和農民。到15世紀,它還是一個主要的經濟中心。大津巴布韋的酋長們做黃金、銅錠和象牙貿易,進口印度玻璃珠項鏈、棉布和海貝等奢侈品。他們非常看重中國的瓷器,認為中國的瓷器器皿比他們自己的黏土制品要好得多。
1497年,第一個葡萄牙人剛剛踏上東南部非洲海岸的時候,大津巴布韋正處在它權力的頂峰。而到16世紀初,馬紹那人已經離棄了這片土地。他們離棄的原因仍是一個主要的謎題,也是許多傳說和想象的敝事中的一個謎。
1871年,德國探險家、黃金勘探者卡爾?莫奇寫下了關于大津巴布韋遺址的報道,他是第一個報道大津巴布韋遺址的歐洲人。
大圍場工藝精湛的石制品,完全不像當地馬紹那人住的簡陋的土墻茅屋,這使得莫奇相信,大圍場和丘堆遺址很可能不是馬紹那人所建造。事實上,莫奇認定,那些廢墟就是公元前900年,來自地中海的示巴女王(《圣經》中朝覲所羅門王以測其智慧)的白人勞工建造的建筑群遺址。
1891年,英國考古學家J.西奧多?本特主持了對大津巴布韋的首次考古發掘。本特受雇于英同鉆石巨擘塞西爾?羅茲。羅茲相信,只要本特能夠找到建造了大津巴布韋的白人文明的珍貴線索,就為白人殖民者對非洲部落領地殖民化提供了科學的證據
本特在大圍場和丘堆遺址中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但他的發現卻顯得撲朔迷離。他發現,許多非洲陶瓷碎片,與外來的中國瓷器器皿、阿拉伯玻璃黃金項鏈混在一起。本特小心翼翼地把這些遺跡與示巴女王聯系起來,并且以“大津巴布韋是非常卉老的”這樣的傳說聊以。
1905年,英同考古學家大?麥基弗登場。麥基弗仔細考察了他所有的發現,他注意到,在大津巴布韋發現的陶器碎片與馬紹那農業社會(這一地區古代和現代同樣繁榮)的陶器有很多相似之處。他還將他在這些遺址中發現的中國陶瓷碎片運到倫敦,讓那里的專家來精確地確定這些碎片的風格屬于哪個年代。據專家們的報告,這種瓷器距今不到500年,根本不可能被古代地中海人把它們帶到大津巴布韋。面對當地白人殖民者的暴怒,麥基弗宣布,當地馬紹那人的祖先在大約1500年修建了大津巴布韋。
麥基弗的發現激怒了當地殖民者,他們對考古發掘進一步橫加阻撓。直到1929年,英國考古學家格特魯德?卡頓?湯普森甚至對丘堆遺址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古發掘。她根據麥基弗的考古發現,利用古代的玻璃項鏈和瓷器,把大津巴布韋遺址的年代確定在公元700年~1200年。1958年,一隊由南羅得西亞國家博物館的羅杰?薩默斯率領的考古學家,運用一種叫做碳-14年代測定法的技術,更進一步精確地測定大津巴布韋的年代。碳-14年代測定法是通過分析一種放射性碳的數量來進行的,這種放射性碳存在于木頭、木炭、骨頭以及其他組織殘骸中。由于植物或動物死后,其放射性碳以我們已知的速度腐爛,或變成另一種形態,這種分析就使得考古學家們,能夠把一件物品的實際年代精確到幾百年之內。薩默斯和他的考古隊的結論是:大津巴布韋建立于公元300年,而于1500年被離棄。
由于在一種地質構造的形成中,巖層的沉積是按時間順序的,所以你越往深處挖,考古地質層就越久遠。因此,這些巖層為考古學家們提供了一種方法,來確定這些巖層中的骨頭、手工藝品以及其他沉積物的相關年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考古學家們在他們認為有機會找到完好巖層的地方挖一些小溝。每條溝里的每一層都經仔細觀察、研究和記錄,不是繪圖就是照相。此外,考古學家們記下了每一層里的所有特征,諸如建筑物地基和手工藝品之類的精確位置。
麥基弗、湯普森和薩默斯從遺址里和遺址周圍仔細挖掘出的馬賽克上,呈現出大津巴布韋復雜曲折的故事。大津巴布韋第一批居民大約在公元300年到達這里,留下很少的四處散落的黏土陶器碎片。那個時候,贊比亞和林波波河(即鱷河)之間的南部非洲的內陸高原――大致為今津巴布韋――人口由許多游牧和農耕社區組成,而居住在這些社區的人的身份,卻消失在歷史中了。從他們留下的陶瓷器皿判斷,首批津巴布韋人很可能是這一族群的一員。因為這些陶瓷器皿在造型和設計上都與考古學家們在這個地區其他地方發現的陶器相似。我們從考古學記載了解到,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建造石墻。
和大津巴布韋的先民一樣,后來者也種植黍和高粱,放牧牛、山羊和綿羊。起初,也許并沒有幾戶人家住在這里。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他們所建造的房基的遺址,山上和谷底都有。那些小屋和今天馬紹那人普通的小屋幾乎一模一樣――泥土和木棍組成的圓形結構,帶有茅草做的錐形屋頂。
最初的石墻是為加固那些修在丘堆遺址上的土屋而建造的。最后,石墻結合了山頂的大部分巨礫,造成許多狹窄的通道和小圍場。
12世紀~14世紀期間,大津巴布韋的規模和重要地位都有所發展。到了那個時候,它是高原東部邊界上幾個十分發達的殖民地之一。
像其他馬紹那人領地一樣,大圍場也是由頭人或酋長絕對統治。人們相信,這些酋長擁有非同尋常的精神力量,通過這種精神的媒介,可以使他們與他們所敬畏的部落祖先發生聯
系。這種與靈界的關聯是酋長們權力的源泉。正是憑借這個源泉,酋長們才能夠向人民索取貢品,并控制這些領地的政治經濟賴以生存的兩大支柱――牛群和貿易。
直到19世紀末,牛群仍是馬紹那人的經濟基礎,也是社會聲望和社會影響的根源。正是這種“牛背上的財富”,使得酋長們能夠獲得并實現他們對領土的控制權。
據考古學上的記載,交換來的玻璃項鏈和其他外國的小玩意,最早出現在1100年前某個時期的大津巴布韋。它們是印度洋的黃金和象牙貿易的觸角最終到達中南部非洲的一個標志。
這種貿易是建立在對非洲的黃金和阿拉伯、印度的象牙貪得無厭的需求上的,建立在季風季節船只能夠從印度駛往非洲并在一年內返回的基礎上的。駛往非洲的船只滿載廉價的棉布、一串串玻璃項鏈、中國和印度的陶瓷玻璃制品,以及其他廉價的小玩意。這些貨物用來交換黃金、銅錠、象牙’、鐵器、奴隸和其他貨物。
大津巴布韋的酋長們,在他們領地上的黃金貿易中,幾乎實現了絕對的壟斷。考古學家們認為,這種黃金是由其他族群的馬紹那人,從這塊殖民地西南部的山野中開采的。礦工們用鎬和鋤頭沿礦脈挖出小礦井,然后采掘黃金。鐵匠把黃金做成項鏈,或把金粉放人羽毛管中以便運輸。顯然,大灃巴布韋的酋長在這個系統中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
截至15世紀,在十來個地區性酋長部落中,大津巴布韋可能已經是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各個殖民地遺址間的間隔,考古學家們斷定,每個酋長部落分別控制著方圓大約160千米的土地。有了足夠的土地,牛群才能進行大規模季節性地游牧遷移。
15世紀末,大津巴布韋達到了它興盛的頂峰。多年以來,常年不斷的霧氣和雨水從印度洋吹到這片谷地,使得這片土地四季常綠。大津巴布韋遺址上風化的巨礫,長年籠罩在灰色云團的旋渦之中。
在這片土地上,最值得注意的丘堆遺址特征,當數堅固的花崗巖擋土墻了,它保護著丘陵西端。我們知道,有人住在大圍場里面,現在所謂的西圍場,就在這種擋土墻后面。肯定丘堆遺址的宗教地位,一個理由是在西圍場所發現的8只神秘的皂石鳥。每只鳥都刻在一個石柱上,高約1.5米。這種鳥很可能代表加冕的犀鳥,長長的脖子、平喙和覆蓋著羽毛的腿。這些柱子上刻著不同的符號,比如像v字形圖案之類的符號。鳥雕刻在最復雜的柱子上,有一只正向上爬的鱷魚。直到今天,考古學家們也不明白這些鳥所蘊含的意義。
丘堆遺址的重要地位的另一個暗示就是,你很難到達那里。津巴布韋人可以沿北坡上一個狹窄的梯形人口登臨頂峰,也可以沿一條狹窄通道蜿蜒而上,到達巨礫環抱的西圍場。但入口顯然是被限制的。
最后的暗示是,歷史上馬紹那人對丘堆遺址的態度。卡爾?莫奇發現,馬紹那人因這個遺址與祖先亡靈相關而非常敬畏它,而且避諱它。
建筑者們在外墻上的精湛工藝尤為突出,外墻有240米長,他們用做得平整精致的石頭包住未經打磨的石料。外墻的花崗石塊被安放在一起成兩條平行線而無須砂漿來粘合。兩排之間的空隙用碎石和未經打磨的花崗石塊塞滿。薩默斯說,石墻是從北口的東面開始修建的,北口是石墻的3個開口之一。顯然,他們從那里開始,順時針方向建造。薩默斯考古隊的結論是建立在石墻高度上的,石墻從北口起逐漸向下斜。它的平均高度為7米,有些地方達10米。石墻上明顯不同的建筑風格也使考古學家們推斷,筑墻的工程是逐步進行的,也許延續了整整50年左右。
篇(10)
“考古是一門科學。”一直從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學者崔大庸,這樣陳述自己的工作。考古是一門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不僅是對于遺跡的考察,還包括歷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研究。小說中的秘術屬于堪輿學,與科學考古沒有關系。實際的考古發掘有一整套嚴格的科學規程,“如果真的如小說里一樣容易,那豈不是拿著洛陽鏟四處挖挖就能挖出來古墓了?”
近十年來,崔大庸這個名字為濟南人所熟悉,是從洛莊漢墓的發掘開始的。
在距山東省章丘市棗園鎮洛莊村村西1公里的地方,
直矗立著一個神秘的巨大土堆。1999年6月26日,修路隊正在施工建設,就近取土的地點就是這座土堆。上午11時左右,修路隊準備再次鏟土時,不可思議的一幕發生了:推土機
鏟子下去,竟然鏟出了一堆銅器。消息很快傳到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時任山東大學考古系副教授的崔大庸很快趕到了洛莊,參加對出土文物的鑒定和對現場的初步勘察。憑借著專業素養和多年的研究積累,他初步判斷,這個被用來取土修路的大土堆,實際上是一座漢代古墓的封土。
1999年7月,崔大庸被任命為考古隊隊長,帶領著由山東大學歷史系和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的考古隊對該墓進行進一步的搶救性調查和清理。此后近兩年的時間里,考古隊先后發掘了36座大型陪葬坑和祭祀坑,并出土了大量罕見的文物:純金馬具和馬飾、駟馬拉車,140件古代樂器。其中的一套編鐘更是被稱為“漢代第一編鐘”。
除了墓葬規模和出土文物,崔大庸還根據帶有“呂”字的20余枚封泥,初步判斷該墓的墓主人是呂后的侄子,呂國的第一任國王呂臺。但也有專家認為墓主人并不是呂臺,而是齊國的一位諸侯王,
雖然主墓室尚未打開,但是迄今為止,洛莊漢墓已經出土了3000多件珍貴文物,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視。2000年,洛莊漢墓的考古發現被列為年度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從畢業后參加了濟南東郊大辛莊遺址發掘工作以后,崔大庸陸續與同事合作在長清仙人臺和雙乳山取得了重要考古發現,然后就是1999年主持發掘了全國聞名的洛莊漢墓,這一路的辛苦和付出,不是一般人看到的小刷子刷土那樣的輕松。
野外考古工作的條件都很艱苦,工作環境差,居住條件也不好,有時是租賃居民的房屋,甚至直接安營于工作現場。洛莊漢墓的發掘,很多人都說崔大庸運氣好,是個“福匠”,其實這只是一種戲言。當時剛開始發掘洛莊漢墓時,誰也不會想到會有這么多發現。隨著工作的深入進行,才逐漸發現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工作過程中及時把握住了機會,能吃苦。才有了更多的發現。
崔大庸說,洛莊漢墓發掘時,一開始考古隊住在一個廢棄的農場辦公室里。房子漏風,漏雨。每當刮風,屋子里就成了一片土海。外邊下大雨,屋內下小雨。當時每人每天只有5塊多錢的生活標準。白天勞累了一天,晚上還要整理繪圖,文字材料,處理數碼照片,為將來寫出科學的發掘報告作準備。有時發現重要的東西,考古隊員還要加班,值班。
曾有人開玩笑說考古隊員“遠看像是挖土的,近看像是刨紅薯的,仔細一看才是考古的”,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差不多。雖然野外考古工作看起來多是些體力活,但其中所包含的科學性卻是最嚴格的。在進行自然科學研究或其它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實驗和課題都可以反復進行,失敗了總結經驗再來一次。但考古則不行。許多遺跡現象,由于年代久遠,只剩下了一些痕跡。這些痕跡在清理過程中如果不十分仔細認真,一旦出了差錯便永遠無法恢復了。因此,在具體考古工作中,必須時刻用科學的態度武裝頭腦,仔細再仔細、認真再認真,這也就有了很多人印象中考古工作者總是拿著個小鏟子和小刷子在工作。
考古發現的大量遺跡都分布在地下。在清理這些遺跡時,大家不得用各種各樣的姿勢去工作,或坐,或蹲,或趴、或臥,而且一工作就是很長一段時間,常常搞得腰酸背痛,甚至因此而落下了一些職業病。對這些,崔大庸全部不在乎:“因為我們知道,也了解自己所從事事業的價值。默默無聞算不了什么,忠于自己的事業是我們無悔的選擇。考古學的魅力外人無從體會。我們是寂寞清苦的,又是快樂充實的。”
崔大庸認為,小說讓更多人認識到了古遺跡的魅力,但是其中塑造的盜墓者的形象對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在洛莊漢墓的發掘過程中,就出現了盜墓者企圖炸開主墓室的事件。崔大庸認為:“對文物來講,留在地下是最好的保護。”但是,隨著全國大規模建設的展開,“現在文物保護的形勢非常嚴峻,大規模基建對地下文物構成了很大破壞。我們目前對地下文物不是發現一處保護一處+而是發現一處發掘一處。考古隊多是跟在施工隊后面進行被動的搶救性發掘,成了“救火隊”,而他則不時擔當救火隊長。這使得文物保護左支右絀,窮于應付,無法從容進行。提高全社會的文物保護意識的工作不可忽視。
現在,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不少老街巷被拆除了,許多古建筑被推平了……一個又一個城市歷史的標志在消失,讓辛苦從事考古工作的崔大庸委實痛心不已。“很多城市都是一幅面孔,沒有歷史,沒有記憶,沒有特色,這是很遺憾的。”
多年來,濟南市市委,市政府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崔大庸認為,保護濟南這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名城,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全社會的文物保護意識,使悠久文明史的見證物得到有效保護。”